close
如果我妹妹在那時刻問我在想什麼的話,我會毫不猶豫地告訴她:我之所以一直隱瞞著我和馬子們幹那件事的原因。是它對我來說太簡單、太容易、太輕盈、太不像一回事;而我又完全不能忍受自己竟然是個一點都不複雜、一點都不艱難、一點都不沈重、一點都不像回事的人。我不肯向我妹妹承認我的性經驗,其實也並非因為它污衊了我的愛情,而是我根本沒有什麼可污衊的。
我們儘可能作一些小小的變化 -- 換房間、換燈光、換衣著、換姿勢、換一切可以換的東西;除了我們的身體。我們在變換著一切的同時,也發現一種變換不去的感覺一直隱伏在我們變換不了的體內:恐懼。我們都在恐懼著我們那太容易厭倦和被厭倦的軀殼。
厭倦與被厭倦,恐懼厭倦和恐懼被厭倦;主動與被動,恐懼著主動也恐懼著被動。這些也都成為例行的儀式。當一切無法變換也無法被變換的時候,我們祇有另外找一個軀殼。
倘使我在燒成一隻小螞蟻的那時就死去,也許不會變成一個祇能例行軀體遊戲儀式的傢伙;要不,也許我的某一部份早在那時就已經燒死了,而活下來的部分祇會去尋找和它同類的軀殼 -- 那些並不喜歡自己的軀殼。
摘自《我妹妹‧我們剩下軀殼》‧張大春
----- ----- ----- -----
四月的最後一天,我蜷縮在床上兩個小時後,想起這個片段。
曾經忽視的恐懼,油然而生。
全站熱搜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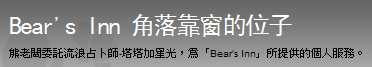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